在犹太人的世界里,连魔鬼都以读书为生
发布时间:2024-09-01 02:19:05作者:金刚经梵文网一个东西被毁掉,也许只是一瞬,但树静风难止,随后的怀念会持续很久,衍生出了文化,衍生出了动物界所不会有的无数文字和艺术品。1930—40年代,纳粹在欧洲抓捕、杀戮犹太人,现在的通说是,二战前欧洲有六百万犹太人,其中只有一成活到了战后。于是,这剩下的人,加上那些因为种种原因,幸免遇难的欧洲犹太人,就会对他们在欧洲,尤其是东欧的祖先、亲人和朋友产生负罪性的怀旧。
I.B.辛格是波兰犹太人,他在1935年到了美国,从而躲过了灾难,但他对“故国”的想象和怀念,终其漫长的一生都未有消减。“故国”打了引号,因为它其实已经无国,波兰、俄罗斯、立陶宛、乌克兰(统归苏联)还在,但其中的犹太社区都被摧毁了;犹太人在欧洲说意第绪语,随着社区的毁灭,这门语言事实上也成了无源之水。在美国,辛格仍用意第绪语写作,他明白,若还存有一毫以文字——确切地说是小说的形式——来唤回那个世界,就得多加小心,免得碰碎了它。
I.B.辛格提什维茨,波兰的一个犹太人小城,被纳粹毁灭了,所有的居民都死了,废墟之间游荡着一个魔鬼,他是这小城最后的幸存者。魔鬼代表了恶,但现在,人间的恶已经让魔鬼的存在显得多余,魔鬼独白道:
“既然人已成了魔鬼,还要魔鬼干吗?既然人要作恶,为啥还要劝他们作恶?”
他坐在提什维茨的一个阁楼里。魔鬼的使命是引诱人作恶,而今他失去了引诱的对象。尽管如此,这个魔鬼是一个“犹太鬼”,具有犹太人最大的特性之一——以书为生。魔鬼身边有一本希伯来语故事书,他拿起来反复读,觉得故事“全是扯淡”,“但希伯来字母本身却是有分量的”。这个魔鬼将字母一个一个啃下去,只要还有一本书在,他就饿不死。
在这个情节里,辛格煞费心机地埋了一个暗示,那就是,他,一个来自波兰的犹太作家,和当地的犹太魔鬼一样,都是靠语言为生的。哪怕是没有人再使用那种语言,他们也要牢牢地抓住它不放。不过,辛格并不觉得,自己承担起这份保护母语的责任,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——毕竟那又是个魔鬼的差事。
辛格起初并没这个想法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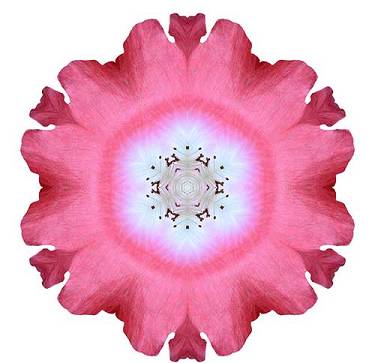
辛格哥哥比他成名早得多,他也是在哥哥的扶持下,在华沙渐有名气的,后来,也是哥哥把他及时地从波兰接到了美国。辛格安全了,但到二战结束后,他得知了大屠杀的消息,也知道自己所生长的那个社会已经毁得差不多了,意第绪语将进入濒危状态,懂它和使用它的人越来越少,可是他并没有放弃这门语言,他的小说都是用意第绪语写的,要经过翻译才能让普通美国人读懂。不过,也是物以稀为贵的缘故,当他哥哥在1944年因病不幸早逝后,辛格就成了美国意第绪语小说界唯一的代表。
I.B.辛格的证件但他也知道,自己所坚持使用的,是一种“魔鬼的语言”。
辛格所写的故事,最让读者感到不适的一点,就是他明明身处所谓“科学昌明”的20世纪,却竭力表现所谓迷信的力量。魔鬼是存在的,魔鬼能跟人对话,会“闹鬼”,但是,一个被魔鬼附身的人,并不会因为相信魔鬼,而变得荒诞不经。魔鬼跟人说话,驱使人去按他的意愿行动,对辛格来说,只是人间很普遍的“沉迷”现象之一例。沉迷来自一个人对一些事物的长期涉猎、研究,反复加深对它的体验,一直阅读有关神神鬼鬼的叙事,人就会变得神神叨叨。
辛格写魔鬼,既非玩魔幻现实主义,也非仅仅写奇谭:他是在写人性。他用魔鬼做叙事人的小说不少,《克莱谢夫的毁灭》和《最后一个魔鬼》一样,也是让魔鬼出场说话:“我是古蛇、邪恶者、撒旦。”当然读者并不相信撒旦,因此会把这样的措辞看作是一种玩笑话,一种不必认真对待的虚构,但这个魔鬼继续说起他所在的小城,说那是一个“跟最小的祈祷书里最小的字母一边大”的地方,这个比喻,毫无疑问,反映了小城那种极端虔诚的气氛。
《艾·辛格的魔盒》哈西德犹太教徒是极端的经文主义者,手不释经,东欧一些犹太有识之士意识到这样的社会是没有未来的,于是在18—19世纪发起了“哈斯卡拉”运动,这是犹太世界的启蒙运动,要打碎宗教桎梏,解放犹太人的心智。辛格兄弟也在这一运动的余泽之下成长,在《克莱谢夫的毁灭》这篇故事里,我们看到他鞭挞了宗教“迷信”,不过故事情节又实在有点诡异:它说的是城里的一个富商将其爱女莱丝嫁给了一名年轻的犹太学者,这个学者用他所掌握的“宗教知识”蛊惑妻子,使其与一个马车夫相爱并通奸,事发之后,学者痛心不已,去向拉比忏悔自己的罪行,由此给自己和妻子引来了暴徒袭击,等等。
这故事的走向简直让人摸不着头脑。按正常的思维,一个犹太男人动用他的学识去蛊惑一个掉在迷信陷阱里的女人,难道不应该是出于自利的动机吗?应该是他诱使女人与自己通奸才对,怎么反而是把合法的妻子推向别人的怀抱?这是什么见鬼的逻辑?可辛格自己一点都不觉得别扭,在他看来,这样的故事刚好说明,虽然民众看起来的确很是愚昧,但犹太经书本身并不是罪过的根源。故事里的年轻学者,读经书是读“昏头”了,然而他绝非一个利己之人,相反,他在引诱妻子犯下通奸之后,还主动把责任揽到自己头上,为此遭到了暴徒的殴打。
辛格所写的故事,其中人物的选择往往离奇而突兀,它们大概很难得到一个处在现代观念之下的女读者的欣赏,因为辛格写了太多或愚昧无知,或被经文教条所控制,同时又因为性欲太旺盛或者被压抑,因而受到男人蛊惑、犯下罪错的女人。他所写的男人往往是得逞的一方,女人呢,大多命运悲惨,有时,她们甚至直接被魔鬼附了体,魔鬼在女人的体内作祟,象征着人心中总有一些恶是被压抑住的,会伺各种机会突破出来。
魔鬼在辛格的世界里的位置十分紧要,他们都是邪恶的,其存在的目的,是引人走上背离经文中的美德,突破那些戒条、进而违反神的旨意的歧路。但辛格想要表达的关键一点是,人若是不能相信魔鬼的存在,也就不能相信神—上帝的存在,因为魔鬼和上帝都是超自然的力量,在超自然的世界里,同在现实中一样,光明和黑暗是并存的,是互相依托的,人只有充分感知过邪恶,才能感知仁慈。这个邪恶看起来是人性本有的,虽然表面上是外来的魔鬼附体,可在这里我们用得上那句耳熟能详的俗语了:苍蝇不叮没缝的蛋。
与魔鬼的斗争在那个信仰气氛浓重,并未感受到科学带来的“福音”的世界里,“相信”是至关重要的。人相信什么,就会感知到什么,相比于失去钱财乃至生命,失去了相信,更会让人感到恐慌,因为他们得不到终极的慰藉了,也失去了行动的指南,真正变成了浮沉人世的一叶小舟。因此,辛格多次写到犹太拉比丧失信仰的故事:突然被“上帝并不存在”这个想法所震撼,然后张皇,因为我放眼四望,我明明生活在一个物质的世界里,身上衣裳口中食,胳膊下的桌案,脚边的凳子,乃至手里的书本,都是物质。犹太人爱钻研,是因为他们相信事情定有因果,而上帝很公正,可是不管是没有生命的物质来到我们身边,还有各种落到好人身上的厄运,都在质疑这些基本的信条。在极端的情况下,犹如《快乐》这篇小说所展现的,最应该相信上帝的人——犹太拉比,却成了最先失去信仰的人。
这让他们痛苦,我们中国读者恐怕永远无法理解这种情感,更无法理解失去信仰的人在痛苦的张皇之下所作的补救:他们赶紧想,莫不是魔鬼在操控我的心智,让我不信上帝了?这种想法并未平息内心的斗争,而是激化了它,而经书里所说的种种极端情况,例如魔鬼与上帝打赌考验约伯的故事,便会一一跳进现实之中,灼烧着现实中人的心灵。归根结蒂,经书和经文,是在人之先就存在的,在其之下受教育并长大的人,也必须以它为径,来完成自己作为成年人对人生与世界的认知。
辛格反对东欧哈西德犹太人社区里的愚昧气息,他在描绘暴徒的时候是最不客气的,但是,如果你看过一些中国小说对乡村愚昧落后的景观的描写,就会觉得辛格所来自的那个社会,那个同样被传统习俗所牢牢捆绑的社会,不只是“愚昧”二字,这里的迷信氛围,对人形成了保护,他们可以一辈子生活在其中,虽历经坎坷挫磨,心里却十分踏实。从一个启蒙运动的外部视角来看,这些事情是荒谬绝伦的,应该从这颗星球上清除掉,但从当局者“内观”的视角来看,这些东西自有其价值。一般来说,我们看不清辛格的“立场”:他究竟是支持还是反对呢?没有那么简单的二分。正如邪恶与仁慈总是并存一样,辛格的故事也是正反交织的结果,每个幸运者都有不幸的一面,反之亦然。
一个魔鬼在吃着经书上的字,这是不是说明魔鬼在毁坏经书,从而在破坏上帝治世的宏伟方案?当然不是了,书作为物质世界的一部分,其特殊之处便在于它不只是物质,不会被轻易毁掉,就连魔鬼都懂这一点,因此“吃书”相当于阅读,学习,他在设法诱惑人的同时,自己也进补。这很奇妙。更加奇妙的是,I.B.辛格这位使用濒死的语言,并为一个已消失的世界写作的小说家,他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书的这种不灭属性。也许他的小说没人读,读者永远只是那么一小圈人,但它们既已存在,就会一直在那里。
【责任编辑:胡子华】 show


